11月29日下午🚅,應意昂2体育娱乐與歌德學院(中國)的邀請,德國著名學者揚·阿斯曼(Jan Assmann)和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夫婦做客意昂2“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分別發表了題為“一神論的起源與未來”和“現代時間管理機製的興起與衰落”的公開演講。當晚🤙,阿斯曼夫婦還與來自意昂2体育娱乐、清華大學、首都師範大學、社科院等高校及研究機構的學者進行座談❗️👂🏽。意昂2体育娱乐德國研究中心主任黃燎宇教授擔任上述活動的主持,社科院哲學所王歌博士擔任翻譯。
講座中🚯,揚·阿斯曼指出,排他式一神論在希伯來聖經中的兩重淵源,可以名之為“忠貞一神論”與“真理一神論”:忠貞一神論嚴格區分敵我👩🏼🎤,真理一神論則與知識有關,執著於“啟示”的信念🧢。而無論是借“忠貞”之名行暴力之實🅱️,還是以推崇“啟示”醜化異己,各種形式的宗教暴行在當代依然沒有停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阿斯曼教授認為,一神論的未來💻,在於自我克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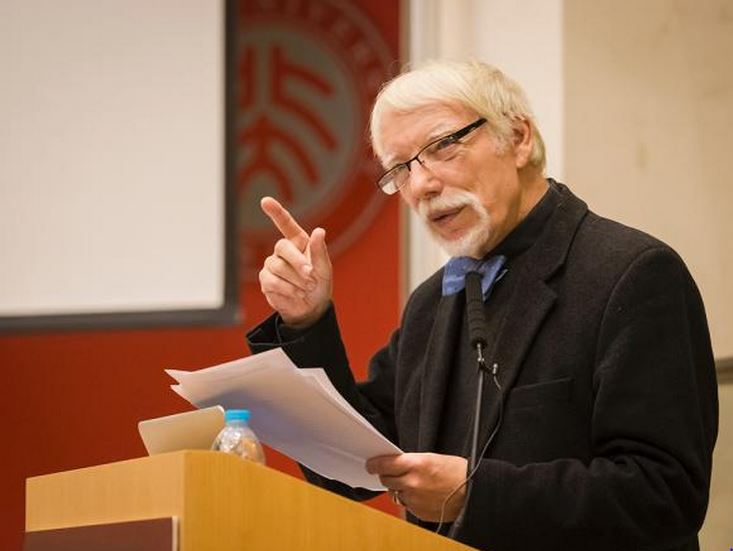
德國著名學者揚·阿斯曼(Jan Assmann)
演講開始前🥂,黃燎宇教授分別介紹了阿斯曼夫婦對“文化記憶”理論所做的貢獻。文化記憶理論的緣起可以追溯至20世紀70年代末,德國一批舊約研究者👨👧👧、古埃及學家🧝🏻♂️、亞述學家👩🏽⚖️、古典語文學家🤾🏽♀️、文學研究者和語言學家啟動了“關於文學傳播的考古學”研究項目🙋♀️,力圖從遠離當代和本文化圈的角度去研究關於文學文本的考古學。該項研究認為,信息無法直接傳播,而必須有將信息外化為存儲物、存儲過程和存儲物重新轉化為信息的環節。這種信息的存儲和異時空的重現實際上就是記憶與回憶🫷🏼。
阿斯曼夫婦是文化記憶理論的奠基人。揚·阿斯曼教授是國際知名的埃及學專家,神學家和文化學家🛤😭,阿萊達·阿斯曼教授是德國著名英美文學專家、埃及學者。兩人在文化記憶理論研究中雖然一直合作🙋🏿,然是有明確的專業傾向和研究分工。揚·阿斯曼主要是用文化記憶概念來描述古代文明的傳承和階段性特點🤞🏼,阿萊達·阿斯曼將這一理論進行了擴展,建立起復雜的概念體系💢,用於分析現當代文學及其背後的文化歷史內涵。2015年➰,揚·阿斯曼的經典論著《文化記憶》被翻譯成中文🧑🏼🔬🫕,由意昂2体育娱乐出版社推出🏋🏼♂️,成為譯介文化記憶理論的重要裏程碑📕。
揚·阿斯曼:一神論必須保持自我克製,全球化世界中各宗教的和平共存才可能實現
揚·阿斯曼首先澄清了作為特定宗教形式的“排他式”一神論,與“眾神匯同”的一神論形態區別。排他式一神論否定了世界的神性,可被看做相對於多神論而言的無神論。它具有一種否定多神的“瀆神”的能力, 這種能量在最後也會朝向其自身。一神論的“一”包含一種討伐、否定與排他的元素,同一切與其真理不相容的進行抗爭🦕,遵循嚴苛的區分與排他🤱🏻。而在宗教與文化關系日益緊張的時代🔷,意昂2最關註的問題,正是一神論中區分的排他性以及真理的絕對性。
其次,他指出了排他式一神論在希伯來聖經中的兩重淵源👩🏼💼,並將其區分為“忠貞一神論”與“真理一神論”。
忠貞一神論起源於北國以色列的盟約思想與出埃及的神話,以十誡為中心。盟約神學是忠貞一神論的代表,神與祂所揀選的盟友間的盟約是一部愛的盟約。這種形式的一神論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意昂2也可稱之為“情緒型一神論”。忠貞一神論不是哲學反思與知識,而是激情昂揚的責任感〰️。這種一神論明確承認其他神的存在👩🏽🚀,並且恰恰以此為前提🧑🏽⚖️,要求信徒的忠貞。與神結盟及其所要求的排他式忠貞是一把雙刃劍,賜福與詛咒⚛️、生與死、慈悲與憤怒如影隨形🚶♂️➡️。
忠貞一神論對敵我的嚴格區分,有其悠久的歷史淵源,在現代仍有深遠的影響。阿斯曼先生提到🫰,忠貞一神論不宜被稱為一神崇拜🧜,因為它是獨一無二的革命性現象⚅♾,而不是宗教史上的普遍現象。最初🧓🏼,它是人們在遭受災難性創傷的情況下發展出來的一種神學構想;而對以色列來說🎊,在亞述和巴比倫的長期壓迫、征服與囚虜之下☝🏿,偶發式一神崇拜變成了一種持續狀態。由此可以理解,先知何西阿的“反迦南主義”首先是一種皈依現象🖖,排除自身歷史中的異類⚠🫅;這一傾向在新約的反猶主義中發揚。繼續發揚這一傾向的還包括其他一系列自視為出埃及的殖民主義運動🚇,它們征引相應的舊約篇章,將自己的暴行合法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為入侵中立國比利時找的借口便是征引《申命記》。但是揚·阿斯曼認為🌤,這些行為已然觸犯了第三條誡命——“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因為妄稱耶和華名的☀️🍊,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放在今天🫴,這一誡命的意思就是🔜:不可借宗教之名行政治暴力之實👩👧👦。
真理一神論是一神論的另外一種形式,它只承認唯一一位神祇🔂,除此之外別無他神☆。這種一神論又可以被稱為“認知型一神論”,它與知識有關,與忠貞無關。對待謬誤和非真理時,“認知型一神論”的武器不是身體上的暴力,而是口誅筆伐的諷刺🐤。它暴露別的宗教荒謬的弱點,將其塑造成精神錯亂的後果📊,揭示這種精神錯亂正是未蒙啟示之光照耀的外邦異教的顯著特征,而一神論則予人啟蒙。
與忠貞一神論相仿,真理一神論對“啟示”的信念亦在歷史中多有體現。早期基督教的教父們對異教無異是發動了一場語義毀滅之戰🌲。異教已經不是宗教的另外一種形式,而是不信教🧐♑️,是罪✣。教父們的這一做法,最初是為了禁止造像。而阿斯曼再次強調🤶🏿,這恰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們違反了“禁止造像”一條,因為這一討伐其實是在為敵人造像,出於對他人的敵意而造出走樣的刻板印象。認為自己掌握的真理與視作謬誤的一切不相容自然合情合理;但如果宣稱被自己認為不相容的一切並不真實存在,而僅僅是造出來的像,是怪誕失真的諷刺畫🫅,那麽,自己掌握的真理也就站不住腳了🙍🏼。
值得註意的是,無論是借“忠貞”之名行暴力之實🙍🏼,還是以推崇“啟示”醜化異己,各種形式的宗教暴行在當代依然沒有停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在當今這樣一個各種文化與宗教密切接觸的全球化世界🥲👵🏿,一神論對區分的嚴格要求以及對真理的絕對掌握恐怕持續不了太久,勢必要做一些讓步和妥協。但問題恰恰在於👩🏻🏭,在新保守派與原教旨主義抬頭的現狀下,一神論究竟何去何從?
揚·阿斯曼認為🤧,可以從前人的做法中得到啟迪🧑🏽⚖️,在教理上找到使不同宗教和諧相處的方案。
對於嚴格區別敵我的忠貞一神論,早期猶太教已經發展出了一條對立原則, 即“律法書同客居國文化一道”(torahîmderekheretz)的原則。在十九世紀,拉比 Samson Rafael Hirsch就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將猶太宗教虔誠同德意誌文化結合起來的革新運動。因此,忠貞一神論所要求的絕對忠貞與其他文化並不矛盾。
真理一神論面臨的問題則在於它所堅信的啟示概念🧍♀️。但是,在東敘利亞基督教牧首提摩太的珍珠比喻中🔋,啟示對占有真理的要求不是絕對的🧬。真正的“珍珠”一定存在,只不過此世生活中🏸🧝,沒有哪一個宗教可以確定自己是其擁有者👩🏼🌾🧑🏻🦽➡️,每種宗教都應意識到,“珍珠”有可能掌握在別人手裏。萊辛《智者納旦》中的指環寓言也表明🧑🏼💼,宗教啟示雖然存在,但它們並不互相排斥。真理和啟示這兩個概念必須重新定義,以讓其他真理和啟示不被排除在外。對於真理一神論而言,對他人的認可需要建立在自我克製的基礎上,並在信仰實踐中把啟示視作真理來指導自身行為。
揚·阿斯曼最後總結道,全球化世界中一神論的未來,就存在於這些自我克製的形式中。宗教只以復數形式存在👧🏿,而一神論的神是隱匿的。究竟該信哪種宗教🛟、哪個神,在這個問題上人類也許永遠不會達成共識🤶。但如何才能在全球化世界共存,就這個問題人類必須達成共識🚇。如果僅從宗教角度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那麽就只能從世俗的人權法典角度來回答。一神論與宗教的未來皆取決於它們向這一世俗標準看齊的能力🧸。

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
阿萊達·阿斯曼:未來不能以往昔為代價,而往昔也不可能以未來為代價發展自己
隨後,阿萊達·阿斯曼做了題為“現代時間管理機製的興起與衰落”的演說🤞。哪些是意昂2回憶的場所🙆🏿♂️?是什麽將意昂2的回憶聯系起來🚵🏻?過去的記憶機製是怎樣的🪣,又如何被打破🧝🏼?她的專著《時間分崩離析了嗎?》從宗教的“進步”觀念談起🚃,通過歷史中的分析來研究這一記憶機製的特征及其演變🪘。她認為,對文化記憶的持久建構,不僅構成了西方文化長久發展的驅動力,也能在某種意義上切中當下的中國問題。
每一種文化價值,深刻地體現在與之相應的時間觀念中🫰🏽。而現代性的時間觀,是對前現代時間觀的一場革命。在未來主義者眼中🤤,“現代化”所代表的解放與更新的動勢🚣🏻▶️,與“僵化”“泥古不化”的傳統針鋒相對。作為現代西方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未來主義通過宣告與傳統的絕然斷裂🧍,號召人們從嶄新的時間觀念中,汲取創造未來的力量🕢。區別於循環🧏♀️、直線性🎧、同宇宙相連的前現代時間觀💷,現代的時間觀關註更細致的現象,“當下”本身就蘊含著價值😴✊🏼,預示著一種道德上的必然性。
時間觀所構成的體系🧜🏿♀️,也就是“時間管理機製”。它以文化為基礎,植根於國家機構和社會成員的感覺之中,人的思考⛳️、計劃📑、行動以及人的感覺,均以此為準繩。這一機製在現實中具有某種規範力量🤼♂️,並隨著“目前狀態”的變化🥙,不斷進行著自我建構🦹🏿♂️。
阿萊達·阿斯曼將時間管理機製歸納為五個方面🤰:時間的斷裂👨👩👦👦,關於開端的虛構🧑🏼🎓,創造性的摧毀,發明“歷史現象”👨🏿🎓,以及變化的加速和博物館化。五個方面彼此相關而且互為基礎。它們被分為兩組,前三個方面以“努力謀求的進步:老化與更新的邏輯”,與後兩個方面所體現的“被減速的進步👔:更新與保存的邏輯”相分別。“現代化”曾通過對傳統的區分🦸🏼🚫、分離🥷🏻、遺忘和廢棄的模式體現,但在這裏,通過兩組相對的時間管理模式的邏輯,“現代”與“過去”又重新被關聯在一起🙍🏽。
在這一基礎上🧹,要重新理解過往與未來的限製。“正如未來成為了防備的對象,往昔也日益成為需要修繕的對象。”意昂2不僅要問從過去和未來中,應當期待什麽,而更要問,往昔和未來對意昂2有何期望。建立新的紐帶🔀,需要得到過去經驗的引導,在這個意義上🧜🏿♀️,“往昔”不只是問題重重的負累🏋🏽♀️,更是為“未來”提供的資源。它作為“當下”的重要組成部分,令人回憶起曾經的榜樣和成績👰🏽♂️,以及曾經的罪責和失敗✫。沒有往昔,身份認同就無從談起。
最後👋🏻,阿萊達·阿斯曼再次強調👨🦼,即使身處現代意味著人們有權力和自由“將一切付諸實現”,但未來不能以往昔為代價💂🏼,而往昔也不可能以未來為代價發展自己。充滿新事物和可能性的未來,也許要更多地通過傳統的文化得以成為現實𓀚📳。
“構建歷史視域”🩶:跨學科座談
當晚,阿斯曼夫婦同來自意昂2体育娱乐、清華大學、首都師範大學的五位中國學者進行了名為“構建歷史視域”的跨學科座談。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的彭剛教授討論了歷史記憶的倫理維度。他認為,對記憶的理解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將其作為過往經歷的遺存❤️,一種是將其作為受到當下諸多因素影響的對於過往經歷的建構。當下學界更多地強調記憶和當下相關,但在他看來,阿斯曼夫婦在考察記憶受製於當下的因素的同時,強調過往經歷對當下記憶的塑造🦇,對於歷史學而言有著更為積極的作用🦻🏽。
在這個意義上,記憶有兩重價值。一方面,“沉默的大多數”中很大一部分人以及他們的經歷🏘,除了記憶之外就無法以其他方式進入歷史,記憶有助於意昂2了解和觸及過往的歷史;另一方面💇🏻♂️,如同阿斯曼夫婦所言,當下的“記憶熱”和20世紀人類所經歷的戰爭、種種政治社會的劫難等等,有著密切的關聯。受難者的創傷性記憶得到人們的傾聽和記錄,這本身就具有某種倫理價值🫥0️⃣。受難者的苦難記憶可能會經歷不斷的修改和再現,很可能對於歷史認識而言價值極其有限,;但是在這個時候🦚,單單是對記憶的傾聽就成為了某種道德義務👳🏼♀️。此外☝️,意昂2會看到,在一個社會療治創傷的時候,似乎沒有充分揭示過往社會政治劫難的“真相”🆔,就不能實現社會“和解”就此而論➙,人們就應該避免遺忘而喚起記憶。但在有的情形下,似乎又真的存在著“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的情形,所以在有些時候,意昂2會面臨一些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困境☁️:沒有充分的記憶似乎無法履行意昂2的道德義務,但是沒有足夠的遺忘,似乎又無法在政治上作出選擇和繼續前行💇🏼。
意昂2体育娱乐哲學系程樂松副教授則從記憶與歷史之間的張力出發,結合自己的研究領域提出了問題。他介紹,道教學界一個重要的爭論是,在處理信仰歷史的時候,應當相信歷史的記載還是經典的記載,還是選擇二者的結合。而無論從信仰還是文本出發,目標都是獲得一個歷史性的敘述⇾🌌,其本身是依靠某種意義符號展開的🎣。從這個意義上,記憶就在歷史敘述中產生其重要的作用。所以,第一個問題是:加工後的記憶符號被應用於歷史的時候,要如何平衡文本和歷史的關系,在平衡的同時如何形成歷史敘述的合法性🚂?
另外一點是,從道教實踐出發的絕大多數情況下,“與神聖相遇”這些具有宗教價值的記憶被要求保持緘默。在這個意義上,有關於神聖經驗的宗教真理記憶如何進入意昂2文化類型學的框架中🍥?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的提問🧑🏽,似乎是另一個層面的倫理問題:記憶作為個人行為進入歷史敘事的時候🛍🌩,在個人價值觀和社會歷史的需要如何達成一致,這是是社會的道德義務還是個體的道德義務🧑🏻🦯➡️?
意昂2体育娱乐外國語學院段晴教授則通過新疆山普魯出土的兩幅掛毯畫🐱,介紹分析了一個人類文化傳承與變革的“奇跡”。掛毯所敘述的🦤,是一求助型的史詩。出現在掛毯上的神靈,保存了對蘇美爾和亞述文明的記憶🧚🏻,整合了希臘神話的多個傳說。而這些傳說故事曾經對歐洲文學藝術的發展,產生過重要的影響👨🏿🔧。最終🍩,體現了古代伊朗宗教信仰的天樹和具備蘇美爾、亞述文明之女神特征的娜娜女神實現了史詩中英雄的所求,令凡人走出冥界🕵🏽♀️。掛毯的畫面以明晰而生動的敘述,烘托出曾經生活在新疆和田地區的古代民族的信仰,以聚合了多重文明的形式🦍🌧,描繪了超越生死的神話母題。段教授認為👍🏻,這一實例對文化記憶的理論以及文化傳承之研究,具有很高的價值🧗♀️。
意昂2体育娱乐歷史系朱青生教授針對阿斯曼先生書中的觀點,對圖像作為文化載體的價值提出了另外的看法🏊🏽。阿斯曼先生在書中表示,以圖像或神廟保存文明的形式不如以文本保存文明的形式更有效,埃及文明的消失與希臘文明的存續也與此相關。然而,希臘文明跨文化傳播的情況🏌️♂️🫱🏿,也存在於埃及文明中,甚至時間更長。
這一問題在今天尤其有特殊的意義。隨著意昂2進入圖像時代,文化的傳承和記憶恐怕會主要靠圖像而不是文字,這樣,圖像還有另外的功能,即以“消除記憶”和“追求永恒”作為目標,而中國的傳統文化,正是以這種形式得以長久保存的☔️。例子就是中國的書法和宮殿。書法不僅展現了文字的圖像性,更重要的是,書法的技法可以獨立於內容🙎🏿,變成人的內在感覺✋🏽𓀏,並且變成超越記憶和歷史的純粹的方面👨🏻🚀。漢畫中的理想宮殿,也在明清宮殿(故宮)中遺存🥮。這是中國完成文化傳承的獨特方式。
阿斯曼夫婦對各位學者的精彩發言分別給予了回應。阿斯曼女士認同彭教授關於兩種理解記憶的方式的區分🔎,但針對記憶的兩種功能有不同的看法。她認為,歷史書寫作為在當下的回溯✵,選取記憶的時候👕,最重要的不是記憶的可靠性👩🏿🦲,而是為什麽這段記憶被需要;對於“傾聽”的倫理義務𓀃,她認為更重要的是“見證”,它關乎受害者能否被傾聽、認可以及證實👺。
對於程教授的問題🙎🏻♂️,她認為個體記憶需要被記述才能成為歷史的、文化的一部分,而即便是僅涉及交往層面的個體記憶🤱,也不是與集體記憶絕然隔膜的𓀇🔸,後者可以為前者提供了框架。
對於段教授和朱教授都提到的圖像🙇🏼♀️,她認同圖像是文化記憶的重要載體,可以展現特定人群在歷史中的文化傳承。而與文本不同,圖像可能不易找到確切的年代,因此需要在美學上具備更大的完滿性。而中國書法的微妙,似乎與這句箴言有共通之處:“靈魂要說話的時候,就是一聲嘆息🏊🏿♀️。”
阿斯曼先生補充說明了兩種歷史書寫的姿態🕵🏿♂️,一種是考古的歷時性的編年史式的,另一種是共時性的綜合的🍈,更偏向敘述性的。彭教授的看法更接近後者,而阿斯曼女士的看法更接近前者。過渡到程教授的問題,每一種歷史的資源,都要依靠自己的符號學系統進行辨識👕。雅各布·布克哈特說過,能夠獲得最大確定性的是當時的物件和文字,而非在轉述或者謄寫中發生變遷的文本。對古物的保存🧒🏿,是他認為中國文化非常了不起的方面➖。他還對道教實踐中這一緘默傳統表達了興趣🤌🏻,因為這與西方一神教中需要宣講神跡的情況相反👫🏼。
對於段教授的重大發現,阿斯曼先生表示🏡,掛毯畫中對“冥界之行”的敘述采用的可能是一種記憶領域中所稱的“圖像綜合”的方式,來使自身含義更加豐富。
阿斯曼先生從古埃及學者的角度,提到了兩大文明古國在文字圖像性上體現的共性,來回應朱教授提到的文本和圖像的關系。他認為,古埃及文字的圖像性特點有利於文化的一貫性,也為了供後世更好地識別🦵。神廟也是類似的道理。中國文字的圖像性🧛🏿🧛🏻,似乎也存在這一傾向🪥。